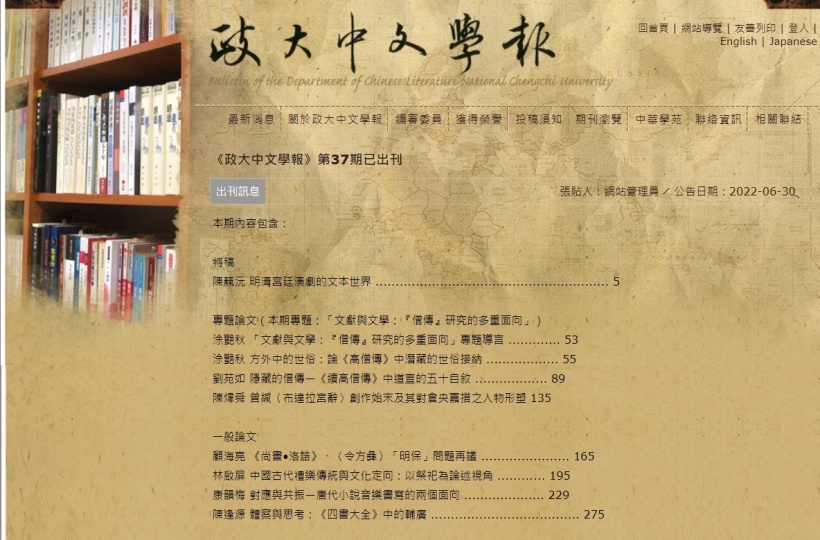摘要:
釋道宣(596-667)繼承了唐代傳記自覺意識、文體多元的傳統,常在諸多著作的序、跋中書寫生平經歷,寄託情感思想,但在所撰的《續高僧傳》反而未見自傳,甚至連自序傳也沒有,僅在諸多他傳中,透過「余」如何如何的敘述,斷裂而隱晦地自我書寫。然經由本文研究即可發現,有別於宋代的各種〈道宣傳〉,或道宣律學著作的自序,其中多屬單一聲部的自我書寫。而道宣在《續高僧傳》中,不僅為「撰者」,同時還「扮演」諸般角色,如學生、共學及晚輩……等不同身分。這些並存的諸多聲影,可視為道宣在貞觀19年以前的五十遊方自述,也可謂是一種自傳記憶。在此試圖發掘這些自傳敘述下所隱藏的諸多訊息,包括主導因素、歷史條件和宗教性,從而探究其人與其時,也即是唐代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及其意義。換言之,就是緊扣道宣個人敘述的同一性,探索其師承與律學系譜,即可發現這些追憶性的話語都籠罩在北朝、隋朝的末法思想之後,亟欲復興佛學的社會框架下,透過晉、并律師行教,以及鄴都律師講律等多重他者的映照,展開種種律學理念的競爭,以加深對其自我律學主張的認知;另一方面,也藉由自己與受業師慧頵(564-637)、受戒師智首(567-635),乃至於親見的法師慧休(548-645)、曇榮(556-640)等的對話,正反辯證,形成可資依從的律學事例。由此展現了其「我是如此」,也更進一步期待促使讀者理解當時諸多僧人亟欲「我們正是如此」,強調佛教內部律法的宗教實踐。
閱讀正文